毫无疑问的是,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成瘾”时代。细数手中的上瘾清单,里面有且不仅有:奶茶、咖啡、游戏、购物、自拍、CP……虽然严格意义上,其中许多或许还不能被纳入“精神障碍”的诊断范畴,但不断加剧并扩展的行为上瘾症状的确正在拓展我们关于上瘾的界定与理解。典型的例子便是2018年,世卫组织首次将“游戏障碍”添加到修订后的《国际疾病分类》中。
为何我们会上瘾?自古以来,我们见过许多说法。例如,成瘾者是过分耽溺于享乐的人;成瘾者就是那些被洗脑、不自制、被操控的人。有时候,人们也会放过一些成瘾者,尤其当他们自带艺术家光环。说到底,人们关于成瘾的看法不太基于严谨的事实,更多是文化与经验塑造下的“迷思”。这也让许多真正处于成瘾状态的成瘾者长期遭受污名化的指摘,更让本该解决问题的戒瘾治疗变形为侮辱性的惩罚。

英剧《梅尔罗斯》剧照。
今天这篇文章,我们就先从关于成瘾者的两种迷思入手,剖析人们对上瘾的常见误解。接着,我们借助最新的成瘾问题研究著作,来理解人为何会成瘾、成瘾如何产生。最后,我们将目光转向当下,厘清“上瘾”消费是如何捕猎年轻人,又如何催生了资本主义在当下的变体。
“丑陋”的成瘾者:
围绕上瘾的两种迷思
这是一种万灵丹,能治愈所有苦痛。幸福,用1便士就能买到。……我似乎每个晚上都要陷入……裂缝和没有阳光的深渊……最后沦陷到彻底的黑暗中,因为一种自杀式的绝望。
有关现代成瘾者最早也是最为直白的描述,出自托马斯·德·昆西在1821年出版的《瘾君子的自白》。尽管上瘾的清单在今天不断扩展,但成瘾的感受不过如此:愉悦与厌恶交织同在。

杰克·凯鲁亚克也是重度成瘾者。据他的自述,《在路上》就是苯丙胺催生的结果。
对成瘾及其机制的界定,目前学术界还未形成统一的定论。一种流行的说法来自医学领域:成瘾是一种脑部疾病。这一观点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由美国国家药物滥用研究所主任阿兰·莱什纳提出,发表于当年的《科学》杂志。
此后,这一说法被广泛引用,美国成瘾医学会等主流权威机构基本沿用这一界定,认为成瘾性物质“劫持”了大脑,使得人们以强迫性的滥用行为取代了选择和自我控制的能力。近年来,“成瘾是脑疾病”的说法虽然遭到学术界的质疑,但它背后蕴藏的化学或药物决定论主张映射着人们长期以来关于成瘾的一种迷思:人之所以会对某些物质上瘾,是因为物质本身的成瘾性。
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许多成瘾问题研究者都驳斥了这一说法。其中,迈雅·萨拉维茨在过去三十年对成瘾问题的研究与报道中发现,单纯接触毒品,并不一定会成瘾。“在接触过最臭名昭著的违法药物——海洛因、可卡因、甲基苯丙胺的人中,只有10%-20%的人最终会上瘾。”她在《我们为什么上瘾》中写道。

《我们为什么上瘾》,[美]迈雅·萨拉维茨著,丁将译,理想国 | 海南出版社,2021年9月。
类似的,英国记者约翰·哈里在遍访实验数据之后指出,如果单单只是毒品导致了上瘾,瘾君子的数量应该比现实情况多得多。这是因为,每家医院都有海洛因(也就是二乙酰吗啡),许多成瘾性物质本身就是病人手术与康复过程中的常备药剂。
按照《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上瘾》一书的作者尼尔·埃亚尔的看法,人们对于物质致瘾的迷思实是一种“斯文加利”式的恐惧。他将这种恐惧命名为“僵尸精神病毒转世”(zombie mind virus reincarnate)。这与人类文明早期对于邪恶力量入侵大脑的恐惧如出一辙。

电影《潜伏》剧照。
另一种关于上瘾的迷思便是,成瘾是一种个人选择,是人的主动失德(事实上,“成瘾是一种脑部疾病”的提出,正是为了回应当时人们对成瘾者的道德化指责)。早在公元6世纪,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就归纳出“七宗罪”,分别是傲慢、嫉妒、暴怒、懒惰、贪婪、暴食及色欲。而后,但丁在《神曲》中根据恶行的严重性将其排序,“暴食”被排在第二。但丁对“暴食”的解释是“过分贪图逸乐”,或可解释为“耽溺”/“沉迷”,其中包括酗酒、滥用药物等成瘾性行为。
事实上,有关上瘾即失德的迷思既拥有漫长的文化传统,也经历过不同的变形。例如,在十八世纪,曾签署过《独立宣言》的美国医生本杰明·拉什将酗酒称为一种“意志疾病”,这一观念的流行直接推动了一百年前的美国禁酒运动。

1919年,美国政府通过了第18条修正案:禁酒令。
但是,没有任何严肃的成瘾问题研究证明过成瘾者一定存在性格或道德上的缺陷。当人们指摘成瘾者是主动选择堕入深渊的时候,往往并非基于事实,而是由政治与文化偏见所带来的刻板印象。人们倾向给成瘾者贴上以下标签:“犯罪倾向、懒惰、暴力、自私、狡诈和爱说谎”。同样的标签也被用以描述弱势群体与外来者。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美国,毒品泛滥的问题时常被毫无根据地归罪于非裔美国人。“人们对可卡因成瘾的黑人的恐惧,正好出现在私刑泛滥的高峰时期,那时候法定种族隔离和选举法的目的都是要剥夺黑人的政治和社会权利。”美国历史学家、毒品政策学家戴维·马斯托(David F. Musto)曾这样说道。
时至今日,失控与失德这两种迷思仍然弥散于人们对于成瘾者的认知中,并与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相咬合。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成瘾者的形象既清晰又模糊。清晰来自于刻板化、道德化的描摹,在各类流行的影视作品中,成瘾者除了病理化的面貌之外,便是人生触底的咎由自取。模糊则来自我们对于成瘾如何产生、又如何被环境与文化塑造的漠视与无知。
成瘾之路:
追寻快乐,还是逃避痛苦?
如何理解成瘾?我们不妨从爱情成瘾说起。在著名的婚恋专家、学者海伦·费舍尔看来,浪漫爱情正是一种瘾。在《我们为何结婚》一书中,她曾提及一项实验:
神经科学家安德烈亚斯·巴特尔斯和赛米尔·泽奇将幸福恋人的大脑同因刚刚注射可卡因或类鸦片毒品而变得亢奋的瘾君子的大脑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大脑奖励系统的不少相同区域都变得十分活跃。此外,我的同事在重新分析了从十七名相亲相爱的男女身上采集来的数据之后(这些数据未经发布),发现伏隔核区域的活性有所提高。伏隔核是大脑的一片分区,对应所有上瘾状态——包括对海洛因、可卡因、尼古丁、酒精、安非他命、类鸦片,甚至是赌博、性和食物的渴望。
费舍尔发现,幸福的恋人会表现出成瘾者的所有行为特征。例如,恋人们会颠倒是非,改变日常习惯,迎合对方;为了让对方对自己留下印象,他们常常会做一些不恰当、危险且极端的事,甚至性情都会大变。
当然,费舍尔关于爱情成瘾的表述,更多可被当做积极上瘾的例子(除非是遇到极端情况),但究其根本,成瘾,正如它的拉丁词根,即是一种“被奴役、被束缚”的关系。无论是爱情成瘾的恋人,还是深受成瘾问题折磨的成瘾者,成瘾之路并非一朝一夕完成,也并非不可被改变。

英剧《伦敦生活》(第二季)剧照。
另一项来自加拿大心理学家、成瘾问题研究者布鲁斯·亚历山大(Bruce K. Alexander)的“老鼠公园”(The Rat Park Study)实验或许能让我们更为真切地理解人为何成瘾。上世纪70年代,医学界关于成瘾问题的研究结论大多来自一项老鼠实验:实验人员把一只老鼠放进笼子,并给它两瓶水,一瓶是普通的水,另一瓶则是掺有海洛因或可卡因的水。结果是老鼠每次都会选择毒品水,并很快因为过量饮用而死亡。
然而,亚历山大教授却认为这一实验少了“环境”这一重要影响因子。于是,他建造了一个被他称之为“老鼠公园”的笼子,里面有老鼠喜欢的彩球、奶酪、玩具隧道,同时,它们还拥有同伴。研究人员也在笼子里放了两个杯子,分别装着普通水和毒品水。出人意料的是:这一回,老鼠们基本不喝毒品水。它们当中也没有出现因过量服用毒品水致死的现象。
这一发现既为人们指出了成瘾并非单纯的物质所致,也为后来的学者开创了从社会文化与心理学角度研究成瘾问题之路。

“老鼠公园”实验的发生环境模拟。
在今天,当我们追问为什么人会上瘾时,包含着两个问题:一是什么样的人容易上瘾?二是上瘾的机制是什么?很多时候,这两个问题具有强关联性。
社会上经常会有一种观点,成瘾者之所以上瘾,无非是想要快乐(在众多关于成瘾问题的探讨文章中,多巴胺理论最多被提及,也常常被片面化理解)。但问题是,如果追求快乐是人的本能,为什么许多成瘾者在后期早已感受不到快乐,还会强迫性地继续?
发展心理学家、《疯狂成瘾者》作者马克·刘易斯(Marc Lewis)曾对此提出,成瘾首先意味着对现实的转移和逃避。也就是说,成瘾者之所以成瘾,是因为他们感觉糟糕,而不是因为他们单纯追求快乐,或是对快乐没有自制力。
许多研究精神创伤与成瘾关系的结果发现,成瘾者上瘾程度越严重,童年经历过的精神创伤也就越极端。在《我们为什么上瘾》一书中,迈雅·萨拉维茨结合自身经历与研究数据结果多次强调,有至少2/3的成瘾者童年期都经历过至少一次严重精神创伤。使用物质,只是他们学会应对创伤的方式之一。
前文提到的心理学家布鲁斯·亚历山大也持有类似观点。他在《成瘾的全球化:一项有关心灵贫困的研究》(The Globalisation Of Addiction:A Study In Poverty Of The Spirit)一书中指出,成瘾是个体对“错位”(dislocation)的适应。它是一种生存型策略,甚至是创造性的反应,在一段时间之内,它可以帮助个体减少“错位”以及无法与周遭环境及社会文化进行心理统合的痛苦。无论这种成瘾是否使用药物,都是一种自我治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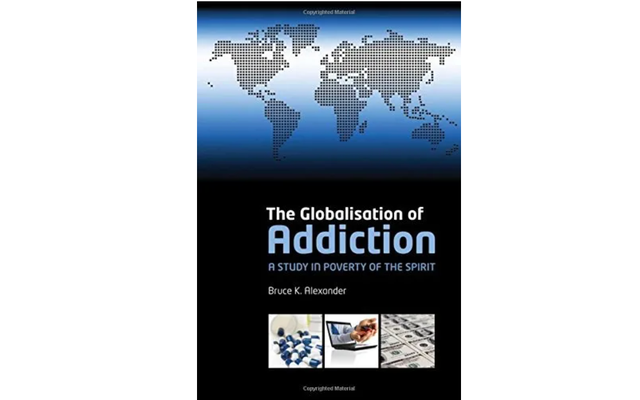
布鲁斯·亚历山大的《成瘾的全球化:一项有关心灵贫困的研究》英文版。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成瘾如何发生?在许多研究者看来,成瘾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学习障碍。萨拉维茨就此界定了三个关键因素:
1)具有心理学目的的行为;2)涉及特定的学习通路,并让这种行为变成自发且强迫性的行为;3)不再有适应性时也不会停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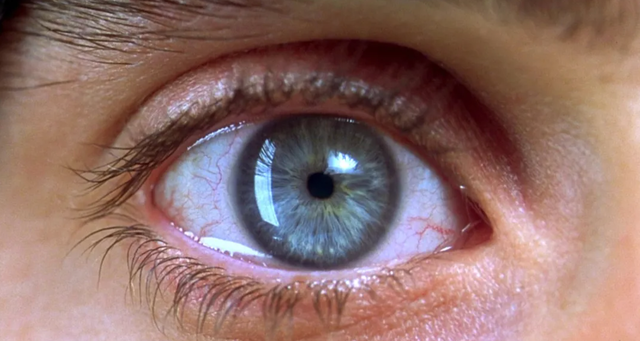
电影《梦之安魂曲》剧照。
心理学家刘易斯则将这种学习障碍称之为“心智习惯”(habit of mind)的养成。与普通习惯不同,“心智习惯”是一种深层习惯,类似物包括种族主义、同理心、厌女症等。重复是其中的关键,帮助大脑强化形成从生物学到心理学的完整反馈路径。同时,重复也意味着一种文化上的习得。
也就是说,成瘾之路并非简单的多巴胺快乐大法,它的背后蕴藏着一整套复杂的运行机制,不仅牵涉生物学/心理学,更有文化与环境的塑造影响。正如布鲁斯·亚历山大所言:“几十年来,关于吸毒成瘾是‘犯罪’问题还是‘医学’问题的辩论一直是徒劳的。一个铁的事实是,它都不是。在自由市场的社会中,成瘾的蔓延主要是一个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
成瘾时代:
当“上瘾”成为消费风口
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其运作的原则就是要挑动人体内的每根神经,并且让它们维持在最高度的人为紧张状态,要把人类的每个欲望逼到极限,并且尽量制造出更多新的欲望与人造的渴求,为的是要我们的工厂、出版社、电影公司以及所有其他从业者制造的产品来满足这些欲望和渴求。
1948年,一位名叫托马斯·莫顿的修士写下这样一段话。他或许不会想到,自己的这番自白竟然预言了大半个世纪后的现实。
身处“成瘾”时代,我们今天的上瘾清单可谓数之不尽,不仅包括烟、酒在内的物质成瘾,也包括游戏、购物等行为成瘾。已有的大量研究发现,物质成瘾和行为成瘾有类似的自然历史。它们产生类似的大脑变化;类似的耐受模式;类似的渴望、陶醉和戒断经历。同时,它们显示出类似的遗传倾向。
尽管行为成瘾者不会那么容易被贴上背德、失信、自私、失控等污名化标签,但这并不代表行为成瘾的危害小于物质成瘾。更值得警惕的是,伴随上瘾清单的不断拉长,成瘾与戒瘾在今天同时成了两门大生意。
2019年,成瘾问题专家、历史学家戴维·考特莱特(David T.Courtwright)出版《成瘾时代:坏习惯如何变成大生意》(The Age of Addiction: How Bad Habits Became Big business)一书,试图从历史中发现全球资本主义是如何塑造、贩卖人们的欲望,并在其中获得自身的演化。
《成瘾时代:坏习惯如何变成大生意》,[美]戴维·考特莱特著,蔡明烨译,立绪出版社,2020年9月。
他将当下这种成瘾性经济称之为“边缘资本主义”(Limbic Capitalism)。在此,考特莱特重新定义了最早由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提出的“边缘资本主义”概念。在萨米尔·阿明那里,“边缘资本主义”是一个经济学概念,相对于作为“中心”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系。
考特莱特所说的“边缘”,指的是脑边缘系统,即负责情感、动力和长期记忆的大脑区域。他对“边缘资本主义”的定义是:一个技术先进但社会倒退的商业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企业借助政府、甚至是犯罪集团之力,鼓励人们过度消费,耽溺欲望。
在考特莱特看来,“边缘资本主义”既是文化进化的产物,与漫长的成瘾性快乐历史交织在一起,同时它也是全球资本主义的邪恶双胞胎,是生产性资本主义的真正癌变。他指出,“边缘资本主义”鼓励企业从人们的成瘾问题中牟利(problem profits),并自动生成围绕成瘾消费的二级与三级利润。他以快餐业为例:当一些人因快餐消费而得了强迫性饮食障碍(compulsive eating disorder),这同时意味着治疗糖尿病与减肥手术的外科医生有了更多生意。

纪录片《大号的我》剧照。
在全球化、金融资本主义与技术的合力下,“边缘资本主义”得以迅速扩张。在一次采访中,考特莱特进一步提到,如果很早以前互联网提供的是选择进入(opt-in)的技术,到了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自由选择退出。在这样的环境中,消费者犹如生活在满是诱饵的海域中。五十年前,这片海域中最主要的成瘾性诱饵是酒精和烟草。现在,诱饵无处不在,难以逃脱。
类似的说法也出现在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的《监控资本主义时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一书中。事实上,成瘾与互联网时代的注意力经济本就难舍难分。许多学者都曾指出,如果人们一味指责那些“看得见”的技术,往往会忽视隐藏在技术与平台背后那双“看不见的手”,也就是所谓的资本力量。说到底,“技术不过是实现利益的手段”。
当我们的脑边缘系统不断成为下一个、再下一个消费风口的目标对象,这才出现了《人物》文章中所报道的“投资人默认准则”。在《「上瘾」消费,围猎年轻人》文章中,接受采访的私募基金投资人王琛(化名)如此说道:“一个能让人深度成瘾的项目,它肯定不是普通的消费品项目,而是更好的消费品项目。”
三十多年前,斋藤茂男在撰写《日本世相》系列时写下:“大环境下,我们眼前一片繁荣,但只要稍微切换舞台,就能看到各类被异化的群体,他们深受各种打击。”或许,我们今天在上瘾消费中看到的,便是切换舞台的世界,看似丰裕的物质生活背后,是一片满是诱饵的水域,与飘荡其间那一颗颗无处可去的饥饿心灵。
主要参考资料:
Alexander, K. Bruce. 2001. The Roots of Addiction in Free Market Society. Ottawa : Canadian 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
Alexander, K. Bruce. 2011. The Globalisation Of Addiction:A Study In Poverty Of The Spiri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美]戴维·考特莱特,《上瘾五百年》,薛绚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8月
Courtwright, T. David. 2019. The Age of Addiction: How Bad Habits Became Big business. Holland, OH : Dreamscape Media, LLC
Zuboff, Shoshana. 2019.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美]海伦·费舍尔,《我们为何结婚,又为何不忠:性、婚姻和外遇的自然史》,倪韬/王国平/叶扬译,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2月
[美]迈雅·萨拉维茨,《我们为什么上瘾》,丁将译,理想国 | 海南出版社,2021年9月
https://medium.com/behavior-design/the-addictive-products-myth-who-is-the-culprit-here-b7a58810f167
https://aeon.co/essays/why-its-high-time-that-attitudes-to-addiction-changed
《「上瘾」消费,围猎年轻人》,人物
https://mp.weixin.qq.com/s/rDDMEwnSbqgBMtHKyqFvKA
作者|青青子
编辑|青青子 李永博
校对|李世辉


加油加油加油